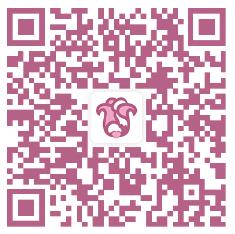精子危机比金融危机可怕
发布时间:2009-11-11
浏览次数:4770
饱受争议的作家张贤亮在沉寂多年后,在今年《收获》第1期上发表了描写未来精子危机的长篇小说《壹亿陆》,引起了一面倒的质疑:题材太过离奇、形式太过荒诞、描写太过低俗。
近日,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这部小说的完整版,张贤亮在上海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。
采写及图片 本报记者 刘放
张贤亮:1936年12月生于南京。上世纪5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。曾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文联副主席、主席,中国作家协会宁夏分会主席等职,并任六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,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。1993年初,作为文化人“下海”的主要代表人物,创办华夏西部影视。其代表作有:《灵与肉》、《邢老汉和狗的故事》、《肖尔布拉克》、《早安朋友》、《浪漫的黑炮》、《绿化树》、《男人的一半是女人》、《习惯死亡》、《我的菩提树》等。多次获得全国性文学刊物奖,获国家与宁夏回族自治区“有特殊贡献的知识分子”和称号。有九部小说被搬上银幕,作品被翻译成27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发行。
“我对我的小说很自得”
广州日报:小说被指“低俗”,你怎么看?听说你自己对小说很自得?
张贤亮:首先,这个小说没有什么纷争。有些媒体说是小说引起了读者的争议、被指低俗,其实是他们自己道听途说的炒作,他们代替了读者和文学评论家在那儿发言,根本就不能代表读者的声音。有一位民工曾告诉我,他春节回家坐了20多个小时的火车,一口气就把小说读完了,并觉得心灵得到了抚慰,看到了生活的希望。这才是读者的声音。
小说中的人物语言的确“低俗”,但那些语言其实都是我根据人物自身的身份、个性来安排的。小说里的性描写,我也写得不低俗、不露骨,适可而止。当然,通过“精子危机”切入小说主题,这种隐喻的写法会被人说成是在卖关子,但我自认为,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把小说的主题传达出来,也只有这样才能把故事讲得好看。
我是对这个小说很自得,说这部小说没有创新、突破,那是一种偏见。我在这部小说里,拿“精子危机”作为故事的入口,展开了一幅当代社会的真实图景,医疗、教育、就业、环境危机和法制漏洞等当今社会方方面面的现实问题,在里面都有反映!当前有几个作家,能有我这样的勇气?我的小说人物、故事、写作手法,都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。
写精子危机是因为欠文债
广州日报:为什么不像以前那样从自己身边熟悉的生活中取材,而要假借一个“隐喻”的题材?
张贤亮:写这个小说最初是因为欠了《收获》杂志一篇“文债”,我答应给他们写一个短篇的,但拖了很久都没动笔。正巧去年9月金融风暴,大家都惶惶不安,我却看到一篇科普类的报道说,金融风暴其实并不可怕,人类现在最可怕的事情是,本身能否延续下去,因为我们人种越来越衰弱,男性精子越来越不行了。我觉得很有趣。以前我就听说过,某地建立精子库,结果来捐献的一百多人精子质量都不合格;还有就是国家权威部门统计,中国每八对夫妻就有一对不孕不育。这就是我们的现实!我就抓住了这个写,本来只是一个短篇的构思,一写就亢奋了,写着写着就变成了长篇。
“我没有影射文怀沙”
广州日报:您的小说里还塑造了一个“国学大师”,有人说是隐射文怀沙?
张贤亮:我也听到了这个说法,那完全是胡说嘛。这个人物在我刚开始写的时候根本就没有,是后来写着写着就自个儿跳出来的。有人说,是两个人都有长长的胡子,所以引起了联想。其实,我这个人物本来就有胡子的,刚好写的时候有个画家到我那儿看我,他留着胡子,我觉得挺好看,就给人物加了个胡子,跟文怀沙完全扯不上边嘛。
广州日报:您好像很看不上韩寒、郭敬明等作家?
张贤亮:我多年来一直关注底层、关注弱势群体,还参政议政了20多年,提出过很多提案。80后、90后的小孩子,也许在艺术性的起点上会比我高,但我已经70多岁了,我的眼界和深度不是二三十岁的人能比得上的。我知道有人认为我很狂,老是表扬自己,我确实从来不吝于表扬自己。我现在已经到了可以狂的年纪了嘛,老了还不狂,什么时候狂?
记者手记
被张贤亮彻底雷倒
因为《壹亿陆》,已经沉寂多年的张贤亮再度成了争议人物。但这次的“争议”几乎是一面倒的质疑。这让张贤亮多少有些不高兴。于是否认有“质疑”这回事存在,“都是你们道听途说的”,然后两眼一闭,毫不留情地溢美自己,“我就是天生异禀……我的小说人物、故事、写作手法,那都可说是前无古人的!”
老实说,有点被张贤亮的这种“自恋”雷到了。一个“取种生子”的故事,谈不上有多离奇多荒诞。问题在于,本来用不着心虚的事情,张贤亮却偏要在叙述中不断强行插入“请别以为作者在胡编乱造”之类的说辞,显得“此地无银”。张贤亮说,他的这部小说非但不离奇荒诞,相反还反映了医疗、教育、就业、环境危机和法制漏洞等当今社会问题,没几个作家有这等勇气。但问题是小说家的“职业道德”应该是至少先把故事说好,何况那些“反映”的问题,其实都是陈词滥调,谁稀罕你在小说里再“反映”一回?